夫妻淫乱实录
夫妻淫乱实录
第一章 妻子的前度男友
我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对于夫妻间的亲热也觉得难为情。所以平时有外人的情况下我总是一本正经规规矩矩拒绝她的亲昵动作,让妻老以为我不爱她。
我总觉得,爱应该在心里。每天挂在嘴上的“爱”也许并不都是真的爱,那些油嘴滑舌的花花公子不是常常说这个字吗?但是,他们有几个是真心的? 但妻显然不这么看。
在和妻谈朋友时,可能因为对她不够关心,让她曾经在我和另一个男人之间摇摆不定,并投到过那个男人的怀抱。
这个男人我见过,妻的同事,在同一个办公室,广东人,瘦瘦的,个子也不高,戴副小眼镜,嘴巴比较大,说实在,长得有点对不起观众。
我也从侧面打听过,他比我大好几岁。或许有俩臭钱,加上仗着本地人,挺能忽悠女孩子的,听说已经和妻公司好几个不懂事的小女孩扯不清了。
妻常说我不关心她的时候,总提起那个男的怎么用蛋清加蜂蜜让她敷脖子上的皮肤病。但那时我挺自信,并不太在意,一是因为我们已经上过床了(现在看来自己那时其实很幼稚),二是我不相信她会弱智到上这样的当。
但妻那时最终没能禁受得住花言巧语的诱惑,在我偏偏不适时宜的出差两个月时,躺到了那个男人的身下。
那段日子用黑暗来描述一点都不过份,相信遭遇过失恋或者爱人变心的朋友都可理解。
只说几件事,就可明白我当时所有的心情。
我每晚要吃两片安眠药才能入睡。
上班有时忍不住跑到厕所里哭,有一次在楼顶哭得头晕目眩,差点一头栽下去。
提着菜刀到那个男人宿舍找她,把薄铁皮门砍了个洞。
在妻的宿舍下面等她一夜,雨也下了一夜,没打伞。
我虽然心灰意冷,但并没有坐以待毙、无所作为,和那个男人拼起了耐心、细心、爱心、虽然这不是我的强项。
我写了一本日记,在后来准备结束时送给妻。可惜,在一次发现妻又到那个男人那里后,我将所有我送给她的东西,鞋子、衣服、包括日记要回,当着她的面扔到垃圾桶里。其中,有这样一首酸酸的诗:
今天来了位妇人
她是个热心的、好心的阿姨
知道了我的近况
温言将我安慰
我尽量显得无所谓
希望她看见了不会太难过
或者太可惜
我喜欢听她说
你是个好的女孩子
可是她也许不知道
我却不是个好的男孩子
不会浪漫
不够温柔
也不能分担
爱人的忧愁
任何一个女子跟了我
都不会感到幸福
你当然也不会
尽管在心里
我仍是这样热烈地
想着你
妻的闺中朋友几乎一边倒倾向我,讲实事摆道理替我做说客。但妻却总是在我和那个男人之间举棋不定,暗地里和他同时保持关系。
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她,她也一而再、再而三的为这个男人背叛我,但最终我们还是走到了一起。说实在的,最后一次答应原谅她时,我是下定了毁灭她的报复决心。
事情的发展出乎我的意料,她对我的好及儿子在她固执坚持下降临,不仅让我下不了抛弃她的决心,甚至为了给儿子一个适当的身份,我还催促她办理了结婚证。之后,我们从不提她的从前,害怕彼此伤害。对我们来说,彷佛从没发生过那样的事情。
我们的性生活趋于平淡,但我们从没停止做过,除了曾经三次短暂分开,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几乎天天都做。
有一些日子(现在也还是),在网上我只浏览淫妻类的文章,幻想妻子被别的男人操得死去活来,尤其是那种特别粗长的鸡巴,青筋暴起,通体油亮发黑,在妻子淫汁横流的肉穴里捅进抽出,刮翻着穴内嫩肉,真的让自己欲火高涨坚硬如铁。
记得再次提起那个人是我主动的,那是一次例行公事的做爱。
我狠狠将整根鸡巴捅进妻子的阴道中,为将要提出的问题兴奋得有点发颤。妻子感觉到我的情绪,拱着身子热切地响应着我。
“爽不爽?”我喘着粗气问她,快速而猛烈地抽动着。我不希望在她十分清醒的情况下问她这个问题,避免尴尬,也不容易动气。
“爽……爽死我了……啊……哦……操死我了!”妻子有点语无伦次,神情有些迷乱。
“爽……是吧?……比他操得爽吗?”我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喉咙“咕噜”一声,艰难地吐出这句话,同时抽插的速度明显快了一些。
“比他操得爽……啊……”妻子兴奋的回答,没有任何犹豫或者羞愧,干脆得让我有些心痛,而且,我感觉到了她阴道壁的收紧及颤抖。
“是不是已经把我和你那野男人比过很多次了?……干死你个骚货……”我兴奋地带着报复的心理狠狠捅了她两下。妈的,我还没提哪个人,她都已经想到他了,肉洞还那么大的反应,八成以为现在插在她骚屄里的是别人的鸡巴。 妻子没有觉察我的变化,淫荡地呻吟着:“好爽啊……老公,你现在最厉害了……操死我了……嗯啊……快点操……”
“谁的鸡巴大?”
“你的……”
“谁操得你爽?”
“你操得爽……”
“他操得不爽吗?”我将妻子的两条腿架在肩上,鸡巴连续三次长驱直入,尽根没入淫水泛滥的阴道内时,前挑后撞,顿时搅得水花四溢、淫声连连。 妻子吃力地张着嘴,断断续续地说:“不爽……啊……爽……爽……死……了……”
“他操得你也这么爽?”我又一次将鸡巴从那温热的阴道内抽离,然后就像工地上的打桩机一样又猛然直直插回去。
妻子舒服得“哦”了一声,淫叫着:“他操得不爽,一点都不爽……老公,你操得爽啊……老公……我离不开你……啊……”她奋力地想擡起头伸着双手想抱我,但我没有放开她的腿,最后她无助地像哭一样“哦哦”叫着,双手从左右两边把两个白肥的乳房不断也紧紧挤压在一起。
“他操得不爽,你还让他操那么多次?啊,你个骚屄,就那么欠操吗?” “我鬼迷心窍……老公……我再也不让别的男人操我了……我永远就要你一个……啊……老公……我的骚屄……啊……是你一个人专用的……爽……” “你的骚屄都被别的鸡巴操烂了,还说是我专用的?”我夹杂着有些变态的快感疯狂地上下坐落着屁股,每一个畅通的贯穿都是那么痛快,都是那么淋漓。 “难道你老公……就只能专用烂屄吗?嗯……操……操死你个烂屄。”我喘气都有些不顺畅了。
“……”妻子的双腿被我压到她胸前,整个屁股高高悬起,身体呈U型,在我快速的冲击下,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哦……我的……骚屄……是被你的……大骚巴……操烂的……操烂了……啊……操死了……”
我有些续不上力,脑袋缺氧似的有些空白。这两年几乎没有什么体育锻炼,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从插入到现在至少有四十五分钟了,这种剧烈的活塞运动太消耗体力了。
我分开她的双腿,然后整个身子覆盖在她热力散射的的温软肉体上。像以前做爱我累了一样,妻子搂紧我的背部,收拢双腿,在她天衣无缝的配合下,臀部的挺落没有丝毫停滞,只是每次的贯穿没有刚才那样彻底、凶狠。
我喜欢在体力不支、妻子又没满足的时候采用这种男上女下覆盖式的传统方式。除了臀部的运动外,全身都可保持在一个放松休息的壮态中,虽然这样会被妻子怀疑有偷懒或例行公事的嫌疑,但同时她也是很喜欢这种方式。
妻子从刚才的狂风暴雨中慢慢回过劲,心疼起我来:“老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再搞嘛……”像条勃发春情的蛇一样缠着我扭动着。
我确实有些累了,伏在她身上不动。妻子立即像八爪鱼一样双腿绞在我的屁股上,双臂紧紧搂着我,生怕我的鸡巴脱离她的阴道,下面的肉腔律动着,时紧时松地咀噬着我的肉棒。
我用脸颊磨着她的耳垂:“你们有没有操过一百次?”我很惊诧自己变得这么开明大方了,记得第一次知道她在那个人那里过夜的时候,我是怀里揣了一把菜刀找上门的。而现在,除了声音兴奋得有些变调外,我没有任何怨恨别人的意思。
“嗯,讨厌……”妻子在我的屁股上打了一下,扭捏起来。
“有没有嘛?”我的屁股动了起来。
“没有……”妻子搂得我更紧了。
“那有多少次?”
“……”妻子似乎在犹豫着。
“老婆,你说嘛,我不会生气的。”边说边加快了抽送的速度。
“四……五次……啊……”在我肉棒的威逼下,妻子又进入状态。
“肯定不止五次,你给我老实交待!骚货,干死你!”亲口从她口中说出,我既兴奋又有些愤怒,狠狠地捅着她。
“真的……没有超过五次……啊……好爽……快点插啊……老公……” “我不信。”我停下来不动:“不说实话,我不搞了。”
“真的老公,就五次……求求你,快点操,操我啊……老公……我受不了了啊。”妻子咬着牙忍耐着,浑身滚烫。
“是你自愿的,还是他强迫你的?”我当然知道是她自己进了人家门还上人家的床,但我还是希望听到她说出另外一个结果。
“……”
“你自愿的……是不是?”
“……”
“是不是?”我把鸡巴抽离至她阴道口,又停下了。
“是……”她赶紧用双手去搂我的屁股。
话音没落,我就猛然一下插进去:“你个臭婊子,竟然掰开骚屄叫人家操!老子今天非操死你……操,非把你的臭屄操烂……还敢不敢叫野男人操?嗯?”我发疯似的快速抽动着。
“不敢了,老公……我再也不敢……叫野男人操我了……你一个人都快把我操死了……爽死我了……啊啊……屄心子都操烂了。”妻子弓着身子,头部不停在摆动着。
我再也撑不住了,一股强烈的快感已经不可阻挡地涌上脑间,我用双手牢牢地捧着她不停摆动的头部,屁股用尽全部的力气向她下面撞击着。
一下,两下,三下,最后深深插进去:“我射……射……嗷……嗷……”我抖搂着,脑袋再次空白,失去意识,一下,二下,三下,随着肉棒几次无比强劲的勃动,一股股精液像火山一样喷放,“滋滋”地打在她的阴道壁上。
妻子张着嘴却发不任何声音,只是不断地吞着口水,喉咙里不时地“咕噜”响。
剧烈的高潮持续了近一分钟,我才无力地瘫软在妻子身上喘息着。妻子像八爪鱼一样死命地把我搂在她怀里,嘴里一边“老公、老公”地淫叫着,一边在我脸上到处狂乱地舔着。
每次游戏结束,我都想快些躺下休息,可妻子总不想那么快放过我,不但不许我马上从她阴道里抽出来,强迫我爬在她身上抱着她,还要跟她说会话才算了事。
待到她的高潮平息后,我屁股擡了擡,从她湿滑的肉洞里拔出肉棒。妻子不情愿地松开手脚,我才得以翻身平躺在床上,湿淋淋的肉棒竟没有疲软,依然直直地挺立着。
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以往精力特别旺盛的时候射过后也会这样,但今天显然例外。
妻子似乎也累得不轻,没有如往常起身擦拭下体的狼藉,娇懒地平躺着,高耸的乳房随着逐渐平缓的喘息起伏着,面如桃花般绯红。
几次不经意的眼神交流,做爱时的毫无顾忌、口无遮拦让彼此都感到有些难堪和尴尬,妻子就没有像往常那样再缠着我说话,翻身背对我而卧。
没有了面对面的直接压力,我们都又沈浸在刚才汹涌澎湃的激情回味中。以往我不愿不想提起这个话题,并不全是我胸襟大度,因为我做为受伤害的一方可以从妻子一生中的内心深处得到一份谦疚。我不提,妻子当然就更不会自揭短处了。这个禁忌今天被我主动打开,意想不到的是不仅没对我们两人的心理制造障碍,反而使我们平淡如水的性生活重燃激情。
我们太久没有这样疯狂地做爱、享受了。
看看妻子侧卧着凹凸起伏、滑如锦锻的腰身,我的心里充满爱意。翻身过去搂住,妻子擡了擡头,左臂便从她脖子下面伸过去握住她的一只大乳。
该面对的始终都要面对,我扳过妻子的脸对着:“舒服不舒服?”
妻子闭着眼忸怩:“舒服……”
我对着她的嘴吻了下去,她挣扎了几下便接受了,并更热烈地啜吸着我的口水、舌头。
好不容易才挣脱,妻子如丝媚眼充满款款柔情,眨巴着注视着我:“老公,我好舒服。你呢?”
“我也是。”我慢慢地抚摸着她说:“……说说他是怎么做的,好不好?” “说什么呀……”妻子娇羞地把头往我怀里钻,“不都一样嘛,有什么好说的?”
“说说嘛,没事的。”我怂恿着:“事情都过那那么久,我早看开了。” “真想通了?一点都不恨我了?”妻子扬着脸问我。
“真的,想通了,就当老子的自行车被贼偷去骑了一圈又找回来了嘛!”我笑说揶揄道。
“你才是破自行车……”妻子娇羞地在我腰上捣了一下,回嘴道。
气氛活络起来,我们就慢慢地说着她和那个男人的事。
我问她,他操得爽不爽?怎么做的?谁在上面?有没有吃过他的鸡巴?一旦放开,她也没了什么顾忌,问什么答什么。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提到那个男人的名字,但都心照不宣。
她说他那东西非常大,很长,跟个驴鸡巴似的,每次都插得很深,从没有完全插进去过,没有和我做得这样舒服,因为他插得她有些痛。姿势也只有一个,他在上面,他做的时间很长,有时能搞一夜,她摸过他的鸡巴,但没有吃过,他也只在她的阴道里射过,不像我,到处射。
问答的过程我们都很兴奋,让妻子翻身背对我,就又插进的的肉洞里。 我又问她,是他的大鸡巴好还是我的小鸡巴好?她说大的也有好处,比方说她喜欢在高潮过后让我抱着她从后面再插进去睡觉。因为我的比较短小,做过后硬度不太好,勉强插进去动一下就会滑出来。而他的就不会,插进去一夜都不会掉,而且也不会软。
她说他们真的一共只搞过五、六次,没有我想象的的上百次那么多。
听妻子说着她姘夫的伟岸,想象着那鸟黑粗长的鸡巴在她自愿敞开的肉洞里肆无忌惮地进出,妒火和欲火交替迸发,烧得我的肉棒坚硬膨胀,拼了命一样的在她阴道里插弄宣泄着。
最后妻子在我疯狂的操弄下达到第三次到高潮,我也一泄如注,精疲力竭。完事后,妻子温情款款地说:“我还是喜欢你的,不大不小,正合适我,搞得我爽死了!”
对于妻子的说辞,我也有点相信。
大概半月后的一次女上男下的做爱对话中,让我半信半疑起来。
当时她抱着我的脖子跨坐在我腿上,屁股一下下擡起落下,深吞浅吐,落下将我的肉棒紧紧扣住时,还会前后磨动两下。她吐着气说:“插得太深,屄心子都麻了,爽死我了!”
我狠捏眼前的两只丰乳问她:“插得深了好,还是插得浅了好?”
她说:“深点好。”
我问她:“他插得深还是我插得深?”
妻子如实回答他插得深,我打了一下她的屁股,醋意十足:“那你还说他操得不爽?臭婆娘,寒碜你老公是不是呀?”
妻子被揭短似的娇羞地把两坨乳肉压到我的脸上使劲蹭着:“他插得太深,只知道痛,哪里会爽嘛?”
我两手抓住她的两片臀肉,使劲地把她往我肉棒上压:“你没有让他不要插得太深吗?”
“他喜欢,我有什么办法?”妻子旋动着丰臀,下体的结合部一片泥泞。 “小骚货,舍命陪姘夫啊?!我看你是犯贱,欠屌!是不是?”我擡起屁股狠顶了她一下。
妻子没有防备,身体被擡高,“啵”的一声肉棒脱离阴道,落下时却没能对准洞口再插回去,肉棒滑到她的屁股后面。
妻子“哎呀”一声,伸手下去抓住了滑腻的肉棒,对准她的洞口,“扑滋”一声又坐了进去:“想跑……我还没爽够……”
“没爽够,那你去找你的大鸡巴姘夫啊!真是贱屄不长毛……”我狠狠地顶着她,带着些醋意和隐隐的期待骂她。
“我就要你的,你的最适合我。”妻子毫不理会地狂动着,磨得我的下体隐隐作痛。
我不再说话,两手捏着她的臀肉,使劲地拉进推出。
禁忌一旦打破,再做爱时,我们经常提到这个男人,每次都会让我们兴奋疯狂、坚硬刺激、淫水飞溅。
我问她还想不想尝试一下大鸡巴的滋味,她说有点想。我说:“那你就去找他,让他再操一次。”她说:“不行,我不会再跟那个男人做了。”我说:“没事的,反正操都操过那么多次了,多一次少一次我也不计较那么多了。”她还是坚决不同意。我还保证不会嫌弃她,还会更爱她,她也没答应。
我不知道,如果她真的答应了,我是不是真的会像我承诺的那样,给她放水洗澡,给她喷洒香水,帮她梳理阴毛,帮她穿戴性感内衣和高贵得体的职业装,然后送她走出家门。
没有戴过绿帽的男人可能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感受,那种醋意和刺激交织的感觉会烧得你无法唿吸,心痛发狂,却又欲火高涨。
真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比方说呕气、亲热、聊性的时候,只要妻子一提到她那个男人的大鸡巴,我就会迅速勃起,欲火焚身。妻子也很惊讶,在她需要而我没有性致的时候就拿这个来刺激我,结果屡试不爽,次次弄得她瘫软求饶我才罢休。
但是,她坚决反对再和那个男人有任何关系。我在略微失望之余颇感庆慰。真的要是同意了,两人再在一起,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旧情复发、食之知味呢?况且那个男人还没结婚,我想任何女人都不会视若无睹的,不管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妻子比我理智,没有因为贪欲而去冒险,我们的儿子如此可爱,家庭如此美好,为什么要去破坏呢?
 绿茶婊
绿茶婊 秋月直播
秋月直播 妖姬直播
妖姬直播 恋人直播
恋人直播 野花谷
野花谷 bob体育
bob体育 亚博体育
亚博体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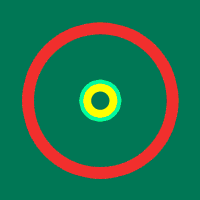 日博体育
日博体育 澳门葡京
澳门葡京 金沙娱乐
金沙娱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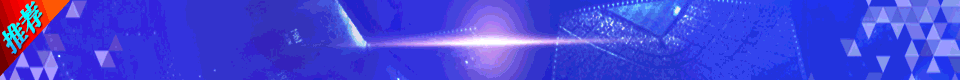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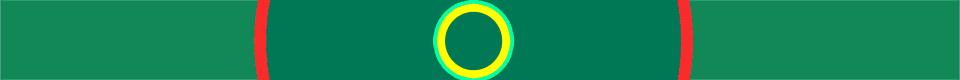
 麻豆直播
麻豆直播 淫妻社
淫妻社 暴走黑料
暴走黑料 猎奇屋
猎奇屋 猫宝
猫宝 Tiktok中文
Tiktok中文 小米视频
小米视频 母狗园
母狗园 大师兄
大师兄 私房流出
私房流出 次元姬
次元姬 半糖次元
半糖次元 午夜福利
午夜福利 小红书
小红书 Acfan
Acfan 夸克视频
夸克视频 好黄站
好黄站 成人吃鸡
成人吃鸡 妖精动漫
妖精动漫